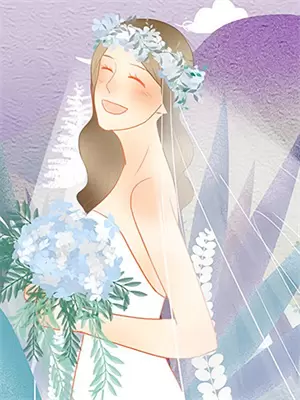
联谊会场里,水晶吊灯明晃晃地悬在头顶,将每张精心修饰过的脸都照得纤毫毕现,空气里浮动着昂贵的香水味、酒气,还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带着点狩猎意味的兴奋。衣香鬓影,杯盏交错,低声的谈笑像一层细密的网,罩着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牢笼。
林晚端着那杯没怎么动过的香槟,指尖冰凉,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沿着她的手指缓慢滑落,留下一道湿漉漉的痕迹。她站在巨大的落地窗边,目光漫无目的地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像在欣赏,更像在逃避。某个方向,有道视线如芒在背,带着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温度——沈亦辰。不用回头,她也能清晰地描摹出他此刻的模样:嘴角噙着那抹惯常的、仿佛掌控一切的得体微笑,眼神却像黏腻的蛛丝,牢牢锁定在她身上。他甚至微微抬了抬下巴,朝她示意,姿态从容笃定,仿佛她仍是那个可以被他轻易召唤过去的林晚。
一股强烈的反胃感猛地冲上喉咙。林晚闭了闭眼,将杯中冰凉的液体一饮而尽,那点苦涩的酒精没能压下心头的燥郁,反而像浇了油。离开他,离开他的一切!这个念头从未如此刻般尖锐清晰。
“各位,”主持人带着职业化的热情嗓音响起,恰到好处地压过了背景音乐,“今晚的重头戏来了!命运的邂逅,全凭天意!请各位女士,移步抽签区,挑选你们今晚的‘专属骑士’!”
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女士们带着矜持又期待的笑容,像一群被驱赶的蝴蝶,纷纷涌向会场中央那个布置得花里胡哨的抽签区。一个巨大的、装饰着俗气彩带的透明亚克力签筒立在中央,里面插满了卷成小筒的彩纸签。
林晚几乎是第一个走了过去。她需要行动,需要立刻斩断那道黏腻的视线。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急促而清脆的声响,带着一种近乎逃离的决绝。她甚至没有看签筒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签纸具体是什么样子,目光只在那堆签里快速扫过,精准地避开了所有靠近签筒边缘、看起来比较整洁、可能代表“优质”对象的签位——那些地方,很可能已经被某些人“精心安排”过。
她的手伸向签筒深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指尖触到一张卷得有些歪斜、颜色也略显黯淡的深蓝色签纸。就是它了!一种报复性的快感混合着自毁般的冲动攫住了她。她用力将那支签抽了出来,动作快得带起一小股风。
展开签纸的瞬间,林晚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了。没有名字,没有编号,只有三个用黑色马克笔潦草写就、力透纸背的大字:
“地狱级。”
旁边还画着一个极其抽象的、龇牙咧嘴的骷髅头。
一丝极轻的、带着浓浓嘲讽的嗤笑从旁边传来。林晚猛地转头。沈亦辰不知何时已悄然踱到她身侧,他微微倾身,凑近她的耳畔,温热的呼吸拂过她的鬓角,声音压得极低,只有她能听清:“晚晚,还是一如既往的……冲动啊。这签,可不兴抽。” 他的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和一种“你看,离了我你果然不行”的优越感。
林晚捏着签纸的手指猛地收紧,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那张深蓝色的签纸在她指间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呻吟。她没理会沈亦辰,目光死死盯着那三个字,一股混杂着委屈、愤怒和破罐破摔的狠劲直冲头顶。地狱级?好啊!再地狱,还能比待在他沈亦辰身边的地狱更糟?
“有意思。” 主持人也看到了签纸内容,脸上职业化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努力挤出更大的弧度,试图缓解这突如其来的尴尬,“看来这位小姐抽中了我们今晚的‘神秘大奖’!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的骑士……”他低头看向手中的配对名单,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夸张,“陆骁!恭喜陆骁先生!请上台!”
“陆骁?哪个陆骁?” “还能是哪个?就那个……去年联谊会上把人家姑娘训哭的那个!” “嘶……‘地狱级’配‘活阎王’,这组合绝了……” “谁这么倒霉啊?抽中他?”
细碎的议论声瞬间在人群中炸开,带着毫不掩饰的同情、好奇和看好戏的兴奋。原本喧闹的会场竟出现了一瞬奇异的安静,所有的目光都聚焦过来,像无数盏探照灯打在林晚身上。
一片诡异的寂静中,会场侧门那厚重的丝绒帘子被一只骨节分明、肤色是健康小麦色的大手猛地掀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逆着门外走廊的光走了进来。
来人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丛林迷彩作训服,裤脚随意地塞在厚重的黑色军靴里,上衣拉链只拉到胸口,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汗衫,勾勒出结实而充满爆发力的胸膛轮廓。肩宽背阔,行走间带着一种长期高强度训练铸就的、近乎野兽般的压迫感。他微微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冷硬的下颌和紧抿的薄唇。嘴角似乎还叼着什么东西,随着他咀嚼的动作,脸颊一侧微微鼓起。
他一步步走向签筒区,步履沉缓,靴底踏在地板上发出清晰的、带着某种特殊韵律的“嗒、嗒”声,仿佛踩在每个人的心跳上。所过之处,人群下意识地向两边分开,自动为他让出一条通道。议论声彻底消失了,只剩下背景音乐还在不识趣地流淌。
终于,他在林晚面前站定。距离很近,林晚甚至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一种混合着硝烟、汗水和某种粗砺皂角的、极具侵略性的男性气息,与他身后那些衣冠楚楚、散发着昂贵古龙水味的男人截然不同。
他微微抬起头,帽檐下的阴影退去些许,露出一双眼睛。
那绝不是一双温和的眼睛。眼窝很深,瞳仁是近乎墨色的浓黑,看人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潭,又像某种瞄准猎物的猛禽,锐利、冰冷,带着一种审视和漠然,直接穿透了林晚精心描绘的妆容和故作镇定的外壳。
他慢条斯理地、几乎是带着某种玩味地,将嘴里嚼着的口香糖吹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泡泡。
“啪。”
泡泡破了,粘在他唇边。他伸出舌尖随意地舔掉,动作带着一种痞气的粗野。然后,他的目光才落到林晚手中的签纸上,又缓缓移回到她脸上,嘴角勾起一个绝对称不上善意的弧度。
“啧,”他开口了,声音低沉沙哑,像是砂纸磨过粗粝的岩石,“娇气包?” 那三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视和一种“你这种温室花朵也敢来”的嘲弄。他微微倾身,凑近林晚的耳廓,热气喷在她敏感的皮肤上,激起一阵细小的战栗,“军营里,可没后悔药吃。”
一股冰冷的怒火混合着巨大的屈辱感猛地冲上林晚的头顶,烧得她脸颊滚烫。她甚至能感觉到身后沈亦辰那饶有兴味、等着看她崩溃出丑的目光。她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用尽全身力气才压下那股想要立刻转身逃走的冲动。
她抬起头,迎上陆骁那双深不见底、毫无温度的黑眸。灯光落进她倔强的眼底,像燃起了两簇小小的火苗。
“谁后悔谁是孙子!” 她的声音不大,甚至因为极力克制而有些微微发颤,但字字清晰,带着一种豁出去的狠劲,清晰地砸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空气里。
陆骁盯着她,墨黑的眼眸里似乎极快地掠过一丝什么,快得让人抓不住。他嘴角那抹嘲弄的弧度似乎加深了零点几毫米,又似乎没有。他什么也没再说,只是伸出那只骨节粗大、布满新旧疤痕和厚茧的手,一把抽走了林晚手里那张写着“地狱级”的签纸,揉成一团,随手塞进了自己迷彩裤的口袋里。动作干脆利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力。
他转身,高大的背影像一堵移动的山墙,径直朝会场外走去,只丢下一句没有任何温度的命令:
“明早六点,南城基地西门。过时不候。”
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嗒、嗒、嗒……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会场里凝固的空气仿佛这才重新开始流动,窃窃私语声如同潮水般重新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