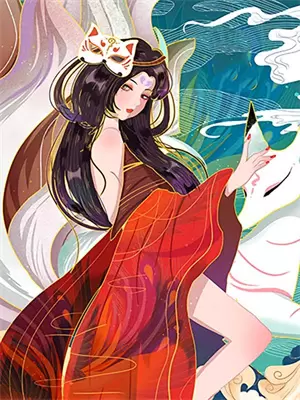林砚秋收剑时,檐角的冰棱刚巧坠下,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响。她抬头望了眼巍峨的朱门,
门楣上“丞相府”三个金字在雪光里泛着冷光——这是她浪迹江湖五年后,
第一次踏回所谓的“家”。引路的老仆见她一身洗得发白的短打,腰间悬着柄不起眼的铁剑,
眼神里总带着几分探究。直到穿过三重庭院,进了书房,
她才看见那位据说病重多年的“父亲”。沈丞相咳着嗽,
枯瘦的手指抚过她腕间一道旧疤:“阿砚,当年你娘怕你卷入宫廷纷争,
才托人送你去了江湖……如今你舅舅登基,朝中总算安稳些了。
”林砚秋握着剑柄的手紧了紧。她自幼在武馆长大,靠替人护送镖银、偶尔管管不平事过活,
从没想过自己的血脉里竟淌着这样的身份——丞相之女,天子外甥女。“江湖人自在惯了,
这深宅大院,我住不惯。”她直言。沈丞相却笑了:“你舅舅说,宫里正好缺个懂武艺的人。
他知你性子野,不逼你学那些规矩,只让你偶尔去宫里坐坐,全了这份亲缘。
”她终究还是去了皇宫。皇帝舅舅比她想象中温和,见她时总带着几分长辈的慈爱,
从不过问她江湖上的事,只偶尔聊些刀剑拳脚。林砚秋渐渐放下戒备,
有时会在御花园里练剑,剑气劈开落梅时,皇帝便在廊下笑着鼓掌:“阿砚这身手,
比禁军统领还利落。”这话传到宫外,成了京中笑谈——都说那位从江湖找回来的相府千金,
空有一身蛮力,不过是仗着皇亲身份才得宠。林砚秋从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
出门时仍穿短打,遇着恶霸便拔剑,惹得不少官员暗地里弹劾她“失了贵女体统”。
转折发生在三月的赏花宴上。那日御花园里宾客云集,文官武将携家眷赴宴,
席间正觥筹交错,忽有十数名黑衣人从假山中窜出,短刀直指龙椅!禁军反应不及,
侍卫们被暗器逼得连连后退,宾客尖叫着四散奔逃。林砚秋本坐在角落喝酒,见寒光袭来,
几乎是本能地起身。她没抽腰间铁剑,只抄起桌上一只玉杯,指节一弹,
玉杯如箭般撞上为首刺客的手腕,短刀“当啷”落地。“护驾!”她喝了一声,
身形已如轻烟掠到皇帝身前。刺客们蜂拥而上,她赤手空拳,
却把江湖上的“沾衣十八跌”使得行云流水——有人挥刀砍来,她侧身避开,
手肘顺势撞向对方肋下;有人从背后偷袭,她足尖点地旋身,反手扣住对方脉门,
轻轻一拧便夺下兵器。不过片刻,已有半数刺客被制服。剩下的人见势不妙,想掷出毒镖,
却被她反手抄起的侍卫长刀挡下。刀光在她手中突然变得极快,快到只看见一道银弧,
刺客们的暗器便尽数被斩落在地。最后一名刺客拼死扑向龙椅,林砚秋足尖踏在栏杆上,
借力腾空,铁剑终于出鞘。没有人看清她是如何出剑的,只听见“唰”的一声,
刺客的蒙面巾被挑落,咽喉前的剑刃泛着冷光,而她剑尖的积雪,才刚簌簌落在地毯上。
满园死寂。方才还在议论她“粗野”的夫人们张着嘴,弹劾过她的官员脸色发白,
连禁军统领都握紧了腰间佩刀——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身手,既有江湖人的凌厉,
又有章法里的沉稳。皇帝抚掌大笑,声音震得廊下灯笼摇晃:“朕说过,阿砚的本事,
你们都没见识过。”林砚秋收剑回鞘,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
转身对皇帝拱手:“举手之劳。”那日后,京中再无人敢小觑这位相府千金。
有人说她剑法通神,有人猜她是某位隐世高手的传人。林砚秋依旧常穿短打,
偶尔进宫陪皇帝下棋,遇着不平事还是会拔剑,只是腰间的铁剑旁,多了块皇帝亲赐的玉佩。
她站在丞相府的回廊上,望着墙外的天空。江湖路远,朱门深似海,可她握着剑,
便不怕前路是哪一种风景。毕竟这双手,既能护镖银过山海关,
也能护至亲于朝堂上——这或许就是她归来的意义。赏花宴上的那一战,
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京城水面,激起的涟漪许久未散。茶馆酒肆里,
说书人把“相府千金徒手退刺客”的故事编得活灵活现,说她剑快如闪电,
能在落梅绽放的瞬间斩落三片花瓣;说她身法如鬼魅,踏雪无痕时连檐下的风铃都不会惊动。
林砚秋偶尔路过听见,也只是掀了掀唇角,
自顾自走进兵器铺——她那柄陪了五年的铁剑在那日格开暗器时崩了个小口,
得找个好铁匠修修。兵器铺的老板是个留着络腮胡的糙汉,见她进来,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计,
搓着手笑道:“林姑娘,您可算来了!上次说的玄铁,我托人从漠北带了些回来,
要不要试试打柄新剑?”林砚秋刚拿起那几块泛着乌光的玄铁,就听见门外传来马蹄声,
是禁军统领亲自来了。他翻身下马时动作还带着几分僵硬——那日在御花园,
他被刺客的暗器逼得狼狈不堪,后来总觉得在林砚秋面前抬不起头。“林姑娘,
陛下召您入宫。”统领拱手时,目光不自觉扫过她手里的玄铁,“听说您要铸新剑?
若是需要上好的淬火材料,我府里有几块西域来的寒铁,或许能用。
”林砚秋挑眉:“统领客气了。”她将玄铁递给老板,“先按原样修,玄铁留着,改日再说。
”跟着统领入宫时,宫道旁的侍卫看她的眼神都变了。从前是好奇里带着轻视,
如今是敬畏里掺着探究。走到御书房外,还没进门就听见皇帝的笑声,里头似乎还有别人。
“阿砚来了?快进来。”皇帝见她掀帘而入,指了指旁边的座位,“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镇北将军,刚从边关回来。”林砚秋看向那位将军,他穿着一身未卸的铠甲,
脸上还有风霜的痕迹,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见她看来,将军起身抱拳:“久闻林姑娘身手,
那日未能亲眼所见,实属遗憾。
”皇帝笑着打圆场:“老将军刚回来就念叨着要找个高手切磋,我想着,
整个京城也就阿砚能陪他过几招了。”林砚秋刚要开口,将军已解下腰间佩刀:“只是切磋,
点到即止。”他刀身一横,刀鞘在地面划出轻响,“我在边关与蛮族交手,惯用沙场刀法,
姑娘若觉得不妥,随时可以停。”她看了眼皇帝,见对方眼里满是期待,
便也解下铁剑:“请。”御书房外的空地上,很快围了一圈侍卫和宫人。
将军的刀法大开大合,带着金戈铁马的气势,
每一刀劈出都像有狂风卷过;林砚秋的剑法却更像江湖路数,灵动刁钻,
总能在箭不容发时避开攻势,剑尖偶尔轻点,都落在将军刀法的破绽处。三十招过后,
将军的额角渗了汗。他猛地收刀,朗声笑道:“好!江湖剑法果然精妙,我这沙场刀法,
竟拿你没办法。”林砚秋收剑回鞘:“将军手下留情了。
”皇帝在廊下拍着扶手笑:“我就说阿砚能行!老将军,这下信了吧?
”将军看向林砚秋的眼神多了几分赞许:“姑娘这身手,若去边关,定能杀得蛮族闻风丧胆。
”这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林砚秋心里。她当晚回府时,沈丞相正在书房等她,
桌上摆着一叠卷宗。“这是近年边关的密报。”丞相推给她,“蛮族总在秋冬时节扰边,
今年更甚,已经占了两座小城。你舅舅愁得几夜没睡,老将军虽勇猛,可蛮族骑兵狡猾,
咱们的人总吃亏。”林砚秋翻开卷宗,里面画着边关的地形图,标注着蛮族的活动轨迹,
还有几处用朱笔圈出的“易守难攻”。她指尖划过地图上的山脉,
忽然想起江湖上护送商队时,曾在类似的山地里设过埋伏,用滚石和陷阱对付过劫道的马匪。
“父亲是想让我去边关?”她抬头问。丞相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刚回来,不想再奔波。
可你舅舅信任你,老将军也看好你……当然,去不去全看你自己。”林砚秋没立刻回答。
她回房后,对着铜镜解下发带——镜里的人,眉眼间还带着江湖人的利落,
可鬓角新簪的玉簪,又在提醒她如今的身份。她摸了摸那柄修好的铁剑,
剑刃上的缺口已被磨平,却留下一道浅浅的痕,像她腕间那道旧疤,都是过往的印记。
三日后,她主动进宫求见皇帝。“舅舅,我想去边关。”她站在龙椅前,背脊挺得笔直,
“不用给我官职,我就以‘信使’的身份去,看看蛮族的路数,或许能给老将军出些主意。
”皇帝盯着她看了许久,忽然笑了:“好!不愧是我沈家的孩子。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人手、粮草,舅舅都给你备着。”“我只要三样东西。”林砚秋说,
“一张最新的边关地形图,十名擅长追踪的禁军,还有……兵器铺的那几块玄铁,
我想让铁匠赶制一批小巧的飞刀。”出发那日,沈丞相亲自送她到城门口。
老仆给她递上一件厚厚的狐裘,丞相却从袖中拿出一枚玉佩,上面刻着“沈”字。
“这是你娘当年的东西,她说戴着能平安。”丞相的声音有些哑,“江湖险恶,边关更甚,
万事小心。”林砚秋接过玉佩,系在腰间,与皇帝赐的那块并排挂着。她翻身上马,
对城楼上送行的人挥了挥手,马蹄扬起尘土,朝着关外的方向去了。同行的禁军里,
有人曾在赏花宴上见过她出手,一路都小心翼翼的。直到进入边关地界,
遇见一小队蛮族游骑,林砚秋才让他们见识到什么叫“高手”。她没拔剑,
只摸出腰间的飞刀。三枚飞刀脱手,像三道银光,精准地射中三名骑兵的马腿。
马匹受惊倒地,剩下的骑兵刚要拔刀,就被她带着禁军围了起来。“留活口。”她勒住马,
声音冷静,“问问他们大部队在哪。”审问时,骑兵嘴硬不肯说。林砚秋蹲下身,
看了眼他靴底的泥渍——那泥里混着沙砾和一种只有黑水河附近才有的红土。
她又看了看对方腰间的弯刀,刀柄上刻着的图腾,是蛮族某个部落的标志,
那个部落往年总在黑水河下游扎营。“不用审了。”她站起身,对禁军说,
“他们的大部队应该在黑水河附近,准备偷袭咱们的粮草营。”禁军们面面相觑,
有人忍不住问:“姑娘怎么知道?”“江湖上混久了,看脚印、辨泥土是基本功。
”林砚秋翻身上马,“咱们抄近路去粮草营,赶在他们前头。”后来的事,
京城里又是一阵传扬——说相府千金在边关料事如神,
用几枚飞刀就识破了蛮族的偷袭;说她跟着老将军勘察地形,在峡谷里设下陷阱,
让蛮族损失了一半骑兵;还说她单枪匹马闯进蛮族营地,割了对方首领的帐篷帘子,
留下一句“再敢越界,下次割的就是你们首领的头”。这些传言半真半假,林砚秋却不在乎。
她在边关待了半年,把江湖上的追踪术、伏击法教给禁军,又跟着老将军学沙场布阵,
身手里渐渐多了几分沉稳的锐气。秋收时,蛮族终于退了兵。林砚秋带着一身风霜回京,
刚到城门口,就看见皇帝和丞相站在那里等她。“回来就好。”皇帝走上前,
拍了拍她的肩膀,“老将军给我写了八封信,每封都夸你,说你是‘边关福星’。
”沈丞相看着她晒黑的脸颊,眼里满是心疼,却只说了句:“先回家,我让厨房炖了汤。
”那日后,林砚秋成了京城里真正的“红人”。文官们不再说她“失体统”,
反而夸她“有勇有谋”;贵夫人们想请她去家里教女儿防身术,连皇子们都想拜她为师。
她却还是老样子,没事就去兵器铺坐坐,或者在城外的竹林里练剑。有人问她,
现在更喜欢江湖,还是更喜欢京城?她望着远处的远山,
手里的剑穗随风轻晃——那穗子是她在边关时,一个小士兵用蛮族的丝线编的,颜色鲜丽,
和她清冷的性子一点也不像。“江湖有江湖的自由,京城有京城的牵挂。”她笑了笑,
抬手挥剑,剑气劈开竹叶,“只要手里有剑,在哪都一样。”风吹过竹林,沙沙作响,
像在应和她的话。远处的皇宫檐角,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光,而更远处的天边,
正有雁群排着队飞过,朝着温暖的南方去——就像她,曾从这里飞走,最终又归来,
却在归来的地方,找到了比江湖更广阔的天地。林砚秋再次踏出国门时,
已不是孤身闯荡的江湖客,而是身负皇命的“持节使”。邻国大燕遣使求和,
提出以皇室联姻巩固盟约,皇帝舅舅思来想去,觉得派谁去都不如派她——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