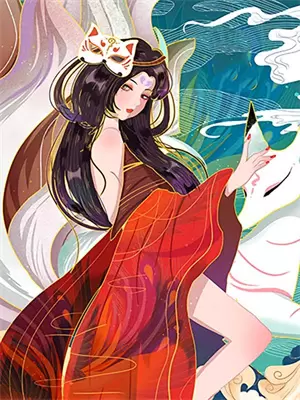一1938年深秋的徐州站,风裹着碎雪沫子横冲直撞,
把站台的铁皮棚顶刮得呜呜作响。赵长河跳下闷罐火车时,
左胳膊的伤口正疼得钻心——那是淞沪战场上留下的枪伤,绷带在撤退途中被泥水浸透,
又冻成了硬邦邦的壳,每动一下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肉。他瘸着腿往站台角落的水房挪,
军靴踩在结了薄冰的青石板上,打滑的瞬间扶住了墙角。就在这时,
眼角余光瞥见个蜷缩在柱子后的身影。是个姑娘。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
外面罩着件浅灰呢子大衣,看料子本该是体面的衣裳,此刻却沾满了泥浆,
下摆还撕了道大口子。她怀里紧紧抱着个铁皮盒子,双臂箍得像要嵌进盒子里,
脑袋埋在膝盖上,露出的半截脖颈在风雪里白得刺眼,像冻住的玉。赵长河咽了口唾沫,
嗓子干得像要冒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凶:“同志,能给口水吗?”姑娘猛地抬起头,
露出张巴掌大的小脸。眉眼很秀气,只是眼下泛着青黑,嘴唇冻得发紫。
最打眼的是她的眼睛,明明蒙着层水汽,却亮得惊人,像被雪光映着的湖面,
猝不及防地撞进赵长河心里。她没说话,只是从脚边的布袋里掏出个搪瓷缸。
缸子边缘磕掉了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皮,她拧开随身带的水壶,倒了半缸温水递过来。
水在缸子里晃了晃,荡出细碎的涟漪。“谢谢。”赵长河接过缸子,仰头灌了大半。
热水滑过喉咙时烫得发疼,却奇异地熨帖了心口的燥——那是连日撤退攒下的疲惫,
是眼睁睁看着战友倒下的堵闷,是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过黎明的惶恐。“你是……当兵的?
”姑娘的声音很轻,带着点江南口音,像被风吹散的柳絮。赵长河把剩下的水喝完,
把缸子递回去:“嗯,暂编第三师的。”他顿了顿,看她单薄的样子,又补了句,
“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姑娘家赶路,得当心。”“我叫苏晚晴,从南京来。”她接过缸子,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铁皮盒子的边缘,“去西安找我舅舅。”说这话时,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像怕被风听见。火车鸣笛了,长而尖锐的声响刺破风雪。赵长河往车厢跑,
军靴踩在冰上发出咯吱声,跑了两步又猛地回头。姑娘还站在原地,风雪吹乱了她的头发,
像株在寒风里摇晃的芦苇。“我叫赵长河!”他扯着嗓子喊,风声太吵,不知道她听没听见,
“到了西安,有难处就去第三师驻地找我!”苏晚晴望着他冲进车厢的背影,
直到绿皮火车冒着白汽驶远,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才低下头看手里的搪瓷缸。
缸底还留着圈浅浅的水迹,像没干的泪痕。她把缸子塞进布袋,抱紧铁皮盒子往候车室走,
盒子里传来纸张窸窣的声响——那是父亲留下的药方,
是她从南京城的火海里抢出来的唯一念想。二半年后的西安城,春寒料峭。
西羊市的青石板路上,挑货郎的拨浪鼓“咚咚”响着,混着茶馆里的说书声,
倒有了几分太平日子的模样。赵长河把军帽往脑后推了推,露出被晒成古铜色的额头,
手里攥着张药材清单——营里不少弟兄的伤口在开春后发了炎,军医的西药早就见了底。
他正琢磨着哪家药铺的黄连便宜,突然听见巷口传来争执声。
几个穿着破军装的溃兵围着个姑娘,为首的络腮胡正扯着姑娘的胳膊,
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着荤话。“放开我!”姑娘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股倔强。
赵长河一眼就认出了那件浅灰呢子大衣——虽然更旧了,袖口也磨破了边。
他把步枪往地上一顿,枪托砸在青石板上的闷响让溃兵们都愣了愣。“干什么呢?
”赵长河往前跨了两步,军靴碾过地上的碎冰,“欺负个姑娘,算什么本事?
”络腮胡上下打量他,见他肩章上是排长的星,啐了口唾沫:“老子们在前线卖命,
找个乐子怎么了?”“她是我师部的人。”赵长河把步枪端起来,枪口对着地面,“再胡来,
别怪我不客气。”溃兵们看他眼神发狠,骂骂咧咧地散了。赵长河这才注意到,
姑娘怀里的铁皮盒子掉在地上,滚出几张照片,被风卷着往远处飘。他快步追上一张,
捡起来时指尖顿了顿。照片上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长衫,
身边站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
背景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门,门楣上的字迹还很清晰。“赵……赵长河?
”姑娘的声音带着颤抖,赵长河抬头,看见她眼角挂着泪珠,脸颊上还有道红印,
像是被人打的。“苏晚晴?”赵长河把照片递过去,注意到她手腕上青紫的指痕,
“你怎么在这儿?找到你舅舅了?”苏晚晴蹲下去捡照片,手指抖得厉害,
几张照片被她按在胸口,像是怕再弄丢。“舅舅上个月去了前线,”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部队说……说他牺牲了。”赵长河心里“咯噔”一下。
他想起自己那个在南京保卫战里没回来的大哥,喉咙发紧。
“那你……”“我找不到地方去了。”苏晚晴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带的钱都花光了,
昨天在城隍庙蹲了一夜。”风卷着沙尘吹过来,赵长河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耳垂,
突然想起十五岁那年,母亲把他推上逃难的火车,塞给他一个蓝布包。“长河,
”母亲的手在发抖,却把包系得很紧,“男人活一辈子,得护着该护的人。
”他解下身上的军大衣,披在苏晚晴肩上。大衣上还留着他的体温,
带着股硝烟和阳光混合的味道。“跟我走吧。”赵长河的声音很沉,“师部后院有间空房,
先住着。”苏晚晴低头看着军大衣上的补丁——是用不同颜色的碎布拼的,
针脚却缝得整整齐齐。她想起南京陷落那天,父亲把她推出地窖,
也是这样把自己的棉袍披在她身上,说:“晚晴,活下去。”“谢谢。”她小声说,
把铁皮盒子抱得更紧了些。三师部后院的那间空房,原是马厩改的。
赵长河找了几块木板隔出个小间,又从老乡家借了张土炕,炕上铺着稻草,虽然简陋,
倒也能遮风挡雨。苏晚晴把铁皮盒子放在炕头的小桌上,打开时,
赵长河才看清里面的东西:除了那几张照片,还有个牛皮纸包,里面是泛黄的药方,
一支银质钢笔,笔帽上刻着个小小的“苏”字,还有个小小的胭脂盒,漆皮已经掉了大半。
“你会写字?”第二天赵长河来送早饭时,看见苏晚晴正趴在桌上写东西,
手里握着那支银钢笔,在烟盒背面写得专注。“嗯,我爹是医生,”苏晚晴抬起头,
把写好的纸递给他,“我跟着他学过几年医术,这些是消炎的方子,
你们营里的伤兵或许能用。”赵长河接过烟盒纸,上面的字迹娟秀,却透着股力量,
药名和剂量清清楚楚。他拿去给营里的老军医看,老军医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突然一拍大腿:“好方子!这几味药搭配着用,比西药还管用!尤其是这金银花配蒲公英,
对付伤口发炎,绝了!”从那天起,苏晚晴成了师部的“编外军医”。每天天不亮,
她就跟着老军医去巡营,给伤兵换药时动作轻柔,碰到伤口溃烂的,她也不皱眉,
只是低着头,用沾了酒精的棉花轻轻擦拭,嘴里还会轻声说:“忍一忍,很快就好。
”伤兵们都喜欢这个说话温软的苏姑娘,有次一个陕西籍的小兵疼得直哼哼,
苏晚晴就给他讲南京夫子庙的糖画,说画糖画的老师傅能把龙画得活灵活现,
小兵听得入了神,竟忘了疼。赵长河常在下训后去看她。有时她在整理药材,
把晒干的艾草捆成小把;有时她在抄药方,借着窗台上的阳光,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马厩改建的房间里,总飘着股淡淡的药香,混着窗外的槐花香,让赵长河觉得心里踏实。
五月的一天,赵长河带回来个青花瓷瓶。瓶身上裂了道缝,是他从被炸塌的祠堂废墟里捡的,
洗干净后倒也能看。“给你插些花。”他把瓶子放在窗台上,
手指有些不自在地抠着军裤的缝,“就是……裂了点。”苏晚晴正在碾药的手顿了顿,
抬起头时,阳光正好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照得像镀了层金。“我爹说,”她突然笑了,
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有裂痕的瓷器,盛得住更多月光。”那天晚上,
赵长河躺在营房的大通铺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第一次觉得这场看不到头的战争,
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他摸了摸怀里的银簪——那是母亲留给他的,说等他娶媳妇时,
就给新媳妇插在头上。四日军轰炸西安城的那天,赵长河正在城外的靶场训练新兵。
先是远处传来几声闷响,像打雷,接着就看见城里升起滚滚黑烟。新兵们慌了神,
赵长河把枪往地上一插,登高望远时,心脏猛地一缩——黑烟升起的方向,
正是师部所在的钟楼附近。“原地待命!”他扯着嗓子喊,抓起步枪就往城里跑。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炸落的碎砖砸在身边,他却像没看见似的,只顾着往前冲。
军靴踩在被炸碎的瓦片上,硌得脚底生疼,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苏晚晴还在师部。
等他冲进师部大院时,后院的马厩已经塌了半边。赵长河的眼睛瞬间红了,他扔掉步枪,
徒手扒着断墙的碎砖,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也没知觉。“晚晴!苏晚晴!”他喊着她的名字,
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在这儿。”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断墙后面传来。
赵长河的心猛地一跳,他搬开块压着的木板,看见苏晚晴蜷缩在墙角,额头上淌着血,
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怀里的铁皮盒子上。“你怎么样?”赵长河把她扶起来,
手碰到她后背时,摸到一片黏糊糊的温热——是血。“我没事,”苏晚晴摇摇头,
把铁皮盒子往他怀里塞,“药方都在里面,别弄丢了。”赵长河这才注意到,
她是用后背抵住了塌下来的横梁,才护住了那个盒子。他突然把她紧紧抱住,
力道大得像要把她揉进骨血里。“傻丫头,”他的声音在发抖,“药方没了可以再写,
你要是没了……”后面的话他说不出来,喉咙像被堵住了。苏晚晴把脸埋在他的胸口,
闻着他身上熟悉的硝烟味,突然觉得很安心。她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像安抚个受了惊的孩子。那天晚上,赵长河在临时救护所守了一夜。苏晚晴睡着了,
额头上缠着绷带,呼吸很轻。他坐在旁边,借着煤油灯的光,看着她的睡颜,
心里做了个决定。五部队要开拔去中条山的前一晚,月亮很圆,
把院子里的槐树影投在地上,像幅水墨画。赵长河在马厩改建的房前站了很久,
手里攥着个东西,手心都出汗了。他几次想敲门,手抬到半空又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