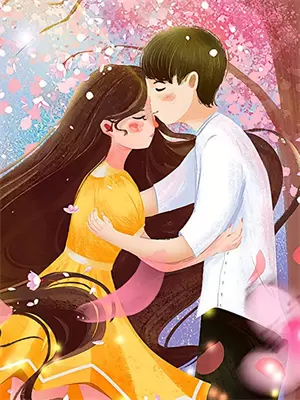支教第一天,破旧小学里,我发现多出的课桌椅总带着泥渍。
暴雨夜看见穿蓝裙的小女孩在槐树下招手,追出去却踩到埋在树根处的儿童骸骨。
当年校车坠崖的死亡名单上,第47个名字被血渍盖住。值日表上歪歪扭扭写着"周小芸",
可所有学生都说,班里从来没有这个人。1槐树的影子像一滩化不开的血,
从教室后窗渗进来时,我右腿的旧伤突然开始抽痛。这是老毛病了,三年前那场车祸后,
每逢阴雨天,骨头缝里就像有蜈蚣在啃噬。我放下粉笔,扶着讲台慢慢转身,
余光瞥见最后一排的空课桌——那张布满黄褐色泥渍的木头桌面上,
又多了几片湿漉漉的槐树叶。“张小河,”我点了班长名字,“这张桌子到底是谁的?
”孩子们齐刷刷低下头,铅笔划过作业本的沙沙声突兀地断了。窗外的蝉鸣乘虚而入,
在死寂的教室里炸开一片刺耳的嗡鸣。“陈老师,”张小河攥着衣角,后颈浮起一层汗,
“没人坐的。”我拄着拐杖往后排走,松动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垂死般的吱呀声。
指尖刚触到冰凉的桌沿,前排的小雨突然打翻墨水瓶,浓黑的墨汁顺着桌缝流到我鞋边,
像一条蜿蜒的小蛇。“对、对不起……”她死死盯着自己涂满红色蜡笔的课本,
肩膀缩成颤抖的一团。那天傍晚,我在值日表上第三次看到那个被涂抹的名字。
“周小芸”三个字歪歪扭扭地挤在周三那栏,像是有人用指甲沾着墙灰写的,
又被红笔狠狠划掉。花名册在暮色里泛着惨白的光,46个名字整整齐齐,
可当我凑近玻璃窗想借最后一点阳光余晖时,呼吸突然僵在喉咙里。起雾的玻璃上,
隐约映出我身后的黑板报。美术字写的“新学期新气象”下方,
多出一排稚嫩的铅笔字——“周小芸今天没来”。冷汗顺着脊梁滑进衬衫后领时,
走廊传来竹扫帚刮过地面的声响。独眼校工老吴佝偻着背,
那只浑浊的右眼在看见我手中的值日表时猛地收缩。他拖着扫帚退进走廊墙角阴影里,
塑料义眼在空眼眶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陈老师,下学了。
”2我是在给小雨补课时发现端倪的。铅笔盒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
却看见她缩在布鞋里的脚踝沾满泥浆——和空课桌下的泥渍一模一样。“小雨,
你早上来学校走的是后山小路吗?”女孩突然抓起红色蜡笔在纸上乱涂,
画本上鲜红的太阳被她戳出个窟窿。窗外槐树枝桠猛地拍打玻璃,我下意识回头,
正看见老吴站在槐树下烧纸钱。橙红的火舌被风卷舔过他残缺的耳朵,
灰烬里飘起一股头发烧焦的臭味。当晚我在办公室整理教案时,山雨叩响了窗户。
十一点零七分,走廊传来啪嗒啪嗒的水声。不是雨声,是湿透的布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动静,
间或夹杂着书包铁扣撞击的脆响。我起身,拐杖撞到门框的瞬间,声音戛然而止。
手电筒光柱切开黑暗的刹那,我差点咬破舌尖——走廊地板上,
一串沾满泥浆的小脚印从楼梯口延伸到槐树下。最大的水洼里漂着片粉红色塑料发卡,
和城里小学生流行的那种一模一样。槐树根部的苔藓有新翻动的痕迹。我蹲下身扒开湿泥,
指甲缝里突然扎进尖锐的异物。摊开掌心,一段米粒大小的白骨在雨中泛着冷光,
像是从什么小动物身上脱落的指节。“陈老师。”沙哑的呼唤惊得我跌坐在地。
老吴举着煤油灯站在三步开外,火苗在他空眼眶里投下跳动的阴影。
他的竹扫帚插在我刚才扒开的土坑里,那些泥浆正顺着帚须往下淌,像极了凝固的血。
“下雨天,”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当心地滑。”凌晨两点,我被雷声惊醒。
闪电劈开窗户的瞬间,我看见值日表在风中狂舞。“周小芸”三个字正在雨水里晕开,
变成一条条猩红的细流,顺着墙缝钻进地板。而在我布满水雾的眼镜片上,
缓缓浮现出更多血字——“陈老师,我坐在第四十七张课桌。”3血字在镜片上蠕动时,
我甩飞眼镜撞翻了搪瓷杯。热水泼在值日表上,那些猩红的笔画突然活了似的扭动起来,
顺着水流钻进地板缝隙。等我哆嗦着捡起眼镜,只剩下一滩铁锈色的水渍,
和46个被晕染成淡红的学生名字。晨读课时,我在讲台上数了七遍。四十六颗黑脑袋,
四十六双高举课本的手,可当阳光斜射进后窗,分明有四十七道影子趴在地板上。
最末尾的那道影子没有头,两条细长的辫子在水泥地上蛇一般游动。“小雨,
”我绕到第三排过道,“昨天的画能给我看看吗?”女孩突然用胳膊压住图画本,
蜡笔“咔嚓”折断在鲜红的太阳里。她的指甲缝塞满黑泥,
和昨天槐树下的泥浆一样泛着诡异的油光。课间操的喇叭突然卡带,
《运动员进行曲》变成尖利的忙音。学生们僵在原地,脖颈以相同的角度转向后山。
等杂音消失,小雨的图画本摊开在桌上——原本画满太阳的纸页间,
夹着一张全新的画:槐树下站着穿蓝裙的女孩,树根处伸出数十只婴儿大小的手。
“这是周小芸?”我指着蓝裙子问。小雨的瞳孔骤然放大,她抓起红色蜡笔捅穿画纸,
在女孩脸上戳出个血窟窿:“她要出来了!要出来了!”老吴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竹扫帚“唰”地刮过门槛,塑料义眼在晨光下泛着死鱼肚白的光。他一把拎起尖叫的小雨,
枯树枝似的手指按在她太阳穴上:“中暑了,我带她去敷凉毛巾。
”我看着老吴拖走不断挣扎的女孩,他的胶鞋在门槛蹭下一块泥,
和空课桌下的泥渍一样混着碎槐叶。4档案室锁芯锈死了,我往锁孔里滴钢笔水时,
闻到一股熟悉的腐臭味——和昨晚老吴烧的纸钱一个味道。铁门吱呀开启的瞬间,
成群的潮虫从1988年的档案盒里涌出来。泛黄的《槐江日报》头版照片上,
校车像只翻肚的甲虫栽在悬崖下。记者用钢笔在死亡名单旁做了标记,
46个名字被血渍晕染,但边缘的横线划了整整47道。最下方有行小字被涂改过,
仔细辨认能看出“遇难者遗体尚未全部寻获”。“陈老师。”老吴的声音贴着我后颈炸开,
报纸在我惊吓中脱手飘到窗边。他弯腰捡纸的动作很不自然,后腰露出一截暗红疤痕,
像是被什么野兽撕掉过整块皮肉。“这树,”他用扫帚尖戳了戳窗外遮天蔽日的槐树,
“有灵。”我顺着扫帚望去,树冠间垂下几缕蓝布条,和画上的女孩裙摆颜色一模一样。
当晚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异常。小雨的造句本第四十七页,
用红笔写着“周小芸坐在我左边”。可这册子明明只有四十六页,
当我翻到本该是封底的位置时,指腹突然刺痛——纸页间夹着根槐树刺,
挑破的伤口正好在指纹中心,像枚鲜红的朱砂痣。5山风撞开窗户的刹那,
远处传来孩童嬉闹声。我扑到窗前,看见后山小径浮着幽幽绿光。
四十七个模糊的小身影手拉手转圈,最中间的蓝裙子女孩突然扭头,
脖子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咔”声,正对上我惊恐的视线。当我手电筒光柱扫过去时,
只剩老吴在树下烧纸。火堆里有什么东西在蜷缩扭动,
爆开的火星在半空组成一张哭泣的孩童面孔。“他们在玩跳房子。
”老吴往火堆扔了把槐树叶,青烟腾起成一道瘦长的人影。“可总有人耍赖,
占着格子不肯走。”我逃回宿舍时,裤脚沾满带泥的苍耳子。正要开灯,
月光忽然照亮窗台上的东西——褪色的粉色塑料发卡,别着一片湿漉漉的槐树叶。
和昨晚在泥坑里见到的一模一样。床头的小镜子在我惊恐中突然炸裂。不是摔碎的,
裂纹是从中心辐射开的,像有人用指尖抵着镜面慢慢施压。当最后一道裂纹延伸到边框时,
我听见小女孩的轻笑:“陈老师,我的发卡好看吗?”镜面炸裂的瞬间,
我抄起枕头砸向窗户。玻璃哗啦破碎的巨响中,
那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变成尖啸:“把发卡还给我!”狂风卷着雨滴灌进来,停电了。
手电筒滚到床底,我在黑暗里摸到个冰凉的东西——是那枚发卡,
断齿上勾着几根细软的黑发。窗外的槐树在雷光中狂舞,枝桠投在墙上的影子,
分明是无数孩童向上攀爬的手。6教导主任踹开门时,我正攥着发卡缩在墙角。
“陈老师做噩梦了?”他用手电照我煞白的脸,“这老宿舍以前是校车司机的休息室,
总有人疑神疑鬼。”暴雨持续到第七天黄昏。留堂补课的张小河打翻墨水瓶,
蓝黑墨水在作业本上洇出个裙摆形状。我掏手帕时,那枚发卡从裤兜滑落,
张小河突然发出窒息的咯咯声,
指着窗外:“周...周...后山…”7后山盘山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
一辆锈迹斑斑的校车正从悬崖方向驶来。没有司机,车头灯却诡异地亮着,
后排车窗挤满苍白的小脸。最右侧的蓝裙子女孩举起手,
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反光——是另一枚粉色发卡。“那是二十年前的校车。
”老吴幽灵般出现在教室后门,竹扫帚滴着泥水,“雨天容易鬼打墙。
”他脚边的污水里漂着片槐树叶,叶脉纹路诡异的拼成“47”。当晚放学我故意留到最后。
八点十七分,锁门的手突然顿住——明明送走了全部46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