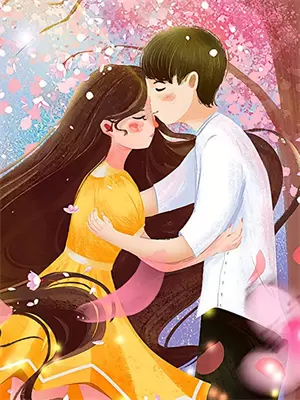有姐长我两岁。
我何时开始失聪的,连父母也说不清了,只知道从记事起就已经听不清周遭,要是有人喊我,非得多喊几声或是离我近些大声些。
乡下的孩童们多得是玩伴,因此都不太爱与我玩耍。
后来母亲说,多半是我太小的时候经常无人照看,啼哭时眼泪流进耳朵导致了病变与失聪。
五岁之前的事我已完全不记得,也不曾问过父母亲,只是隐约知晓一点。
大约我出生不久一家人就到了母亲乡里,但我家没有房子也没有积蓄,父母都是小学民办教师,我们的生活条件是父母微薄的工资和学校狭小的老宿舍。
好在外公家境尚好,时常接济一点。
我三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两年后弟弟出生,从此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
记得母亲生下我弟弟后坐月子的营养品就是煎一个鸡蛋切开几份吃一天。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产假,母亲很快就继续边教课边带着我们。
弟弟还是婴儿,母亲要背着他上课,姐姐上小学了,我无人照看。
母亲刚好教一年级,就让我坐在她的班里上课。
虽然那时我已经听障严重,但小学的东西没有难度,就这么启蒙了。
二我的记忆从这时开始。
父亲在外地上大学,我在母亲的老家上了两年小学。
母亲忙得无暇顾及我,有时候我是跟着外公外婆和舅舅。
他们虽然爱我,但是我的听力很难和他们交流,常常一个人趴在河边看鱼虾看水波,常常一个人看着大人们忙碌孩子们戏耍,什么也参与不了。
我多希望有个伙伴。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毕业了,去了镇里的完全中学教书,也带走了全家。
母亲转了公办,和父亲在同校管理图书馆,我在镇里继续上小学。
镇里的三年小学,我能记起的依然很少。
小时候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周岁时候险些被传染病带走,所以我的身子非常瘦小,又加上听障,成了个别不良同学的霸凌对象。
一个姓林的同学从我转学同班起几乎每个课间都会欺负我打我,所幸也有善良的同学时常保护。
有一次,几个不良同学对着学校围墙外一个社会人喊绰号,一个壮汉冲进来喝问是谁喊的,大家都把手指着我。
而我完全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被打翻在地。
老师也不敢多事,只是怜悯地扶起了我。
这类事我至今没有和父母提起。
那时候只觉得是我自己犯了错,而我这样一个失聪的孩子,原本就是累赘,更不敢诉苦。
那个林姓同学初一依然和我同班,依然常常打我,我依然不敢告诉身为本校教工的父母。
你可能会问我,父母从来没带你去检查治疗吗?一来家里太穷,二来也许我只是累赘。
父亲也关心我,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书看。
但是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来我家和父亲聊天,我学着大人的样子跟老师问候,父亲却皱着眉头很嫌弃地挥手叫我走开。
那一刻我脆弱的尊严被撕得粉碎的感觉,至今如刀痕般刻在我的心底。
从那以后,我害怕与人交往,如果有父亲在场,我更是噤若寒蝉。
我生怕我是不是又听错了什么,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
也许,我并不是错在听错或说错什么。
我也终于知道高三毕业时,一位女生为什么在毕业留念册上说我小时候的绰号叫“累赘”。
父母为什么不带我去做个检查,小时候我压根不会想到要问为什么。
父母是天,他们自然会照顾好我们的。
只是,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记忆中父母亲从来不曾对我有过温馨与亲热的时刻,从记事起父母亲不曾抱过我抚摸过我甚至不曾牵过我的手,所以有一年我生病父亲背着我去医院的画面就成了特别珍贵的记忆。
我和父亲至今唯一的一次接触,是五年的前一天,我六岁的儿子玩游戏将我的手放在了父亲的手中。
那一次我看到父亲的神情是那么的复杂,而我差点流了眼泪。
八十年代教师的工资很低,也不像现在可以课外辅导挣外快,父亲当了教导主任,我们家还是很困难。
别的同学每个季节都有几套新衣、穿上最流行的蝙蝠衫牛仔裤的时候,我一年只有夏冬两套新衣,是母亲去裁缝店做的,袜子是常年露脚跟脚趾的。
到了镇里后,母亲借钱买了台缝纫机,每天下班后缝账本贴补家用。
材料要从几里外用箩筐抬回家,一只箩筐装满账本可能有七八十斤,缝好后再抬回去。
父亲也许太忙,也许拉不下面子,所以是我和母亲去抬。
我上小学时没量过身高,但是十岁上初一时才1米27,我每天放学后帮母亲一份份理账本,一份份剪好线,抬回去再抬回来,从小学到初中。
我因为能帮助父母觉得自己有用,所以每天都很勤快,但是在每天的重担下,我的身高几不见长。
父亲是特别优秀的教师和领导,很快就评了高级职称,又升了副校长,但我们家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给我每周的零花钱是两毛钱,我每天的愿望就是攒到换一块钱的大票,再藏到枕头底下压平。
当时县里开发了一个新镇,土地相对便宜,父母梦想在那里盖个房子,属于我们的房子。
三初中时我的学业开始因为听障而严重下降。
小学毕业考班级前三,初一就跟不上了,坐第一排也基本听不清老师讲课,需要理解的理科瞬间垫底,全靠记背的文科勉强撑着。
印象中父母不曾关注过我的学习,一来我已经很用功,二来可能他们认定我只能如此了。
有趣的是数学老师为了照顾我,还特意把我选进他的奥数小组,我很受鼓舞,天真地以为我是有潜力的,哪怕十道题只对一道,仍然全力以赴。
这位数学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因为我父亲很关照他,他也是一位正直且富有同情心的好老师。
对我冷淡的是班主任,一位家境豪富的语文老师。
尽管我的语文成绩很优秀,甚至我能在半节课里背出一篇文言文,仍旧无法让她对我这个尘埃一般的学生有丝毫好感,无法免除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挖苦我。
至于同学们,偶尔会取笑我,其余时间我是空气。
他们要么成绩优秀,要么家里有钱,要么人高马大,而且我因为过早启蒙的缘故,比同班同学要小两三岁,无论我如何准备,似乎都不能融入他们。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是友善的,只是我的听力与他们交往困难。
多年的经历让我自卑到了极点,我努力想做好一切:拼命读书,拼命抄英语,拼命背理科公式,体育课上咬牙跑到嘴唇发青,凭借书画特长课外给学校出黑板报,但是喧嚣的校园依旧无人多看我一眼。
我当时可能没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该读好书,所以课堂听不见就课后找班长借笔记抄,一遍一遍地背。
教室墙上的标语告诉我天下无难事,数理化再难,我全背下来总能克服困难。
结果我三门理科加起来还是只有一百分左右。
初一那年,林姓同学课间打我的时候,我不知怎的,没有再抱着头哭着挨打,而是跟他扭打在一起。
说起来他也是个瘦猴,但是懦弱的更瘦小的我,被他霸凌了整整四年。
打完人生第一次架后,我在校园角落痛哭了一场。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后来我们又分了班,四十年了再未有他的一点消息。
我的听力依然糟糕。
右耳听不太见但没有严重病患,左耳的情况变得不太好,中耳炎流脓加剧,经常起床发现脓水打湿枕巾。
情况严重了父亲就带我去镇上诊所开药,再严重就打针。
父亲是我的偶像我的天,我还以为诊所的针药能治好我的中耳炎。
初中毕业的暑假,耳疾爆发,左耳靠太阳穴处鼓起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父亲还是带我去那家诊所,那位好看的医生阿姨看了一眼紧张极了,对父亲说我先给孩子打一针,你马上带他去市医院。
八十年代的交通不好,父亲第二天带我去了市医院。
挂号就诊,医生脸色很难看,语气非常不善地责怪父亲不顾孩子。
得知父亲是中学校长后,医生更是语气严厉,说我情况很不好。
拍X光时,需要把我的肿瘤位置贴紧在平台上,我疼得咬牙流泪,但是没有哭出来。
医生看了片子和化验单再检查,确诊是“胆脂瘤型中耳炎”,进一步发展就是脑膜炎,有生命危险,要马上住院安排手术。
由于耳后也鼓起了脓包,手术前要清脓,医生让我坐在椅子上,抓着靠背,手术刀就划开了脓包。
明明是打了麻针的,为什么那么痛?鲜血顺着我的脖子一路流到瘦削的胸口,再流到腰上。
我咬着牙流泪,没有哭出来,也不敢颤抖。
为了省钱,父亲退了晏公殿巷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只靠在我病床旁休息,一个月后出院时,我白胖了些,父亲却更加瘦削了。
隐约听得他和医生对话,医生说手术难度高,最好是从杭州请医生下来主刀,但是额外费用不菲,父亲立即央求医生安排最好的医生主刀,费用没有问题。
我只知道那年的治疗光是请了杭州主刀医生就花去了父亲一年的工资,那时也没有医保一说。
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父母不爱我,他们之前没带我治疗,之后也没给我配助听器,也许贫穷是原罪。
四初中毕业后,唯一的朋友阿挺同学考取中师离开了我,而我没考上高中。
在那个年代,中考比如今高考还难。
幸运的是父亲是学校副校长,政策照顾我升学。
回想起来,辍学的结局我根本不敢去想。
“破格”升学的我,成绩格外的难看。
初中的理科已经是我无法接受,何况高中。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废物,唯一不知道的是我未来会有多废,高中毕业就是我人生终点。
我渐渐接受了命运的裁定,除了徒劳的用功,把自己埋进书堆,翻遍了母亲的图书馆。
高一暑假,我身高才150,体重75。
看着操场上矫健的运动员,自卑极了也羡慕极了,觉得他们是火炬而我只是烛光。
那年暑假我发誓要成为强壮的男人,从母亲的图书馆里找到一套《健与美》杂志,整理出来锻炼方法,抄写画图,再从校办厂那里讨了一对5公斤的生铁哑铃。
那时的暑假没有补习班,我也不可能奢望能出去旅游,哑铃陪伴了我两个月。
尽管没喝过牛奶,也很少能吃肉,我还是长了五公斤的肌肉,也是从那时起,我保持健身至今。
也是那年暑假的末期,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女生。
五梅子不是学生,她在姑妈的修表店里做学徒。
一次校外偶遇女同学,梅子和她一起。
梅子不避生,和我也说了几句话,便说会来找我。
第二天傍晚,我正在宿舍走廊洗碗,梅子来了。
梅子身材高挑,眉眼秀丽,我依然收藏着一张当年她赠与我的相片,海边少女,穿着当时街上流行不久的蓝色牛仔裤,青春极了,妩媚极了。
是的,我和你们一样,丁点都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女生会看上我——矮小、卑微、贫穷、土气的小男生,但当时我幸福极了。
一个从来无人关怀无人陪伴的落魄少年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繁花少女,会是怎样的迷醉。
对于十四五岁的我来说,哪里懂得爱情,她是我的珍宝,除了她的美丽,便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束光。
没有学生身份的梅子,热情开放。
她没有我的犹疑和腼腆,她仿佛是田野里的紫云英,灿烂,自在。
那个夏季,我也如灿烂自在的紫云英。
父亲自然不会允许我和梅子来往,一年后,父亲调动去了新镇创办新校,又带走了一家人。
我们的五层楼房子也基本竣工,一楼出租给作坊,二楼是简单的家具床铺,上面的暂时没铺设楼梯楼板。
因为家里又没钱了。
而我人生的第一朵花,凋谢在那个火热的夏季。
转学到新校读高三读文科班后,人生第一次有了色彩。
大概是那个环境适宜我,不几天就融入了班级。
那一年我格外活跃,给女生做颜值排名,给男生展示我的六块腹肌,还因为与同桌女生早恋而让班主任苦恼不已。
同学们对我这个“怪物”异常接纳,带我参加了很多私底下的活动。
感激他们给了我不一样的一年,我的读书生涯中唯一有色彩的一年。
在毕业纪念册的留言上,一位男生记述我每次语文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还经常第一名,且交卷后总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那一年,我的听力应该没有变化,但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个正常少年。
热情,活力,并且夸张。
因为理科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我从高中开始学画,准备考美术专业。
我从小学开始喜欢上绘画,父亲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连环画,我特别喜欢临摹武将。
有一年暑假,我把全校教室的黑板都画满了武将,每一个武将都大到整黑板的高度。
那一次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充满激情也画得最好的一次了,可惜那时照相机是奢侈品,没能留下印迹。
六高三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美术天分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高考落榜了,去了杭州美术培训部集训复读。
这时候家里条件稍好,但是我知道家里盖房子欠了不少债,而且还有三层楼没有铺设,经济还是非常拮据,所以到了培训部开始学习后,吃饭我都不和同学们一起,而是买了瓶玫瑰腐乳,一顿饭夹出一块就能对付了。
食堂阿姨是美院教授的夫人,有时心疼我,会把我父亲送给她的特产虾干蒸两只给我。
后来我找到不远处的海军食堂,价格比较便宜,能吃上蔬菜和一点肉类。
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培训部学习,租住在玉皇山一户农家阁楼,早出晚归。
然而我原本计划一年的学习仅仅两个月就意外结束了。
一个周末,我从阁楼下来休息,不知怎的,往一楼房间玻璃缝里瞧了一下,黑乎乎的什么也没看见。
过了一会农家阿姨出来,大声斥责我偷看她洗澡。
当时我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自然没有解释,只是很懦弱地躲开了,后来同伴告知了我,我委屈极了,可也明白自己有口难辩。
农家有个独生子念小学,同伴告诉我他精神有些问题。
一天晚上我在阁楼学习文化课,他手持针筒冲了上来,神色扭曲,大骂我偷了他的零花钱。
他父母虽然带走了儿子,但是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善。
作为父母,总是更相信自己孩子的,何况我还有“前科”。
离开杭州的导火索是自行车被偷。
因为不想给父母太多负担,我把一个月的开销控制在二百元以内,包括伙食费大约每天五六块钱样子,节省出三十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以便每天晚上去杭大上文化课,省下长期乘坐公交车的开支。
一个晚上,九点半下课的时候,我发现自行车被偷了,我无助地站在空荡荡的校门口,一遍一遍地寻找我的车子,最终绝望了。
公交车都已停运,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出租车我也坐不起。
我看着玉皇山的方向,终于崩溃了。
那是深冬的寒夜,我一个人走在寂静冰冷的马路上,很快就迷路了。
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只知道身上越来越冷。
走了很远很远,终于走到了西湖。
我沿着湖岸一直往前走,希望能靠近玉皇山,我就能找到“家”,就能缩进温暖的被窝,就能好好睡一觉。
路上见到一个岗亭,一个年轻的警察发现了我,询问后给我指了路。
我感激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问了他的名字叫张勇,接着我又迷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我冷到浑身哆嗦,有些恍惚起来,看到湖边有个亭子,亭子地板上铺着简易地毯,不自觉地过去掀开地毯,躺在地板上盖上了毯子。
不远处是旷淼的西湖,我的耳朵听不见一丝的风声和水声。
那个夜晚,世界从来没那么安静过。
那一刻,我只想回家找妈妈。
记不得怎么回去的了。
同伴把我的那些遭遇告知老师,老师打电话通知我父亲。
两天后,父亲来接我回家。
离开农家和培训部时,我默默地感知着背脊上无数复杂的目光。
七从杭州回来后,我的状态非常不好。
整日如行尸走肉,捧着书本看不进一个字,自然也无法画出一张满意的作业。
特别是去过杭州后,我才发现我那所谓的美术天分,其实啥也不是。
无人理解,无人倾诉。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只魔鬼,只不过别人的魔鬼温顺得多,而我这只被孤独、冷漠和嘲讽豢养了多年的魔鬼,仿佛随时都会把我撕碎。
对于我的状态,父母根本无能为力。
当时姐姐高考也落榜了,在学校打字室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复习重考,弟弟在读初中,他的成绩特别优秀,是我们家的希望。
两个月后,县里组织了一个美术培训班,邀请北京的美院老师来教课。
父亲为我报了名,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由于一直没有做过检查,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听力的具体情况。
如果是面对面交流,我能听见一些,因为我强迫自己锻炼出了一点看唇语的能力。
但是在培训班的人群里,我听不清老师的一句完整话,只能从勉强听见的零散字词里猜测与组织老师的原话。